|
当代中国的政治文化话语场域(文论)
——从拉康的视野看
◎
杨小滨
拉康晚期的“四类话语”理论被拉康学者认为是拉康晚年对文化政治领域的重大贡献,但却并不是拉康理论体系中最广为人知的部分。曾有拉康学者指出:“拉康的四类话语理论……的最大贡献在于意识形态批判和文化批评的领域。”
齐泽克对拉康的阐述当然也始终关怀精神分析的学说中关联到社会政治领域的方面,他认为“拉康的四类话语图式意味着在话语的社会链接之中的四种主体位置”。“四类话语”理论是拉康在1969-1970年间的研讨班(总标题为“精神分析的反转面”,收于拉康的《研讨班文集》第17辑)上最初提出的,主要的意图可以概括为阐述如何理解“主宰(社会)的是语言实践”。很显然,拉康是在1968学生运动的时代背景下,将精神分析理论从哲学和精神科学领域推进到社会文化领域(“精神分析的逆转”研讨班上的内容是拉康学说中最为直接政治性的)。
“四类话语”理论展示了四种不同的政治文化角色——S1(signifiant-maître,主人能指)、S2(savoir,知识)、a(objet
petit a,小他物)、$(le
sujet clive,分裂主体)——之间由于处在不同地位上而形成的四种互动关系。在这里,“主人能指”代表了某种具有统领性、纲领性意义的符号,它武断地占据了首要的位置,比如“神”、“天堂”、“领袖”、“英雄”、“太阳”、“灵魂”,等等。“知识”指的是某种体制化的结构,包括各种工具化、系统化的社会或文化机制,它们是建立在某种以理性法则组构的框架内的。“小他物”在拉康理论体系中占有重要地位,它指的是拉康的“符号界”所无法整合的那一部分“实在界”的残余,是往往以亟需填补的空缺样态出现的欲望的原因-目标。而“分裂主体”概念则是拉康对笛卡尔式主体的修正,将弗洛伊德关于精神病患主体性分裂的论述扩大到一般主体,揭示了主体自身的非同一性。那么,具体而言,四类话语指的是这四种角色在下列图式中的不同位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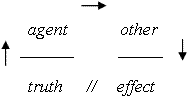
动因
他者
——
——
真实
效应
在这里,“动因”当然是话语的发生者,占据动因位置的角色决定了话语的性质。“他者”则是动因的信息诉诸的对象,或者说是由动因所作用的,但同时他者的存在是话语发送的必要条件。如果说横杠之上标明的是显在的元素,横杠之下标明的便是隐在的元素:“真实”是话语动因深处的原因和支撑,而“效应”则是话语作用的结果。也可以说是,每种话语的构成都是由内在“真实”所支持的“动因”通过对“他者”的作用而产生的“效应”。这样,四种角色循环式地占据了动因的位置,并产生了四种不同的话语模式,即
以“主人能指”为动因的“主人话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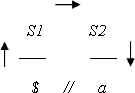
以“知识”为动因的“学院话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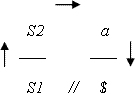
以“小他物”为动因的“分析师话语”(但齐泽克常常强调它的结构与“倒错话语”相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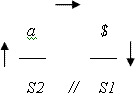
和以“分裂主体”为动因的“癔症话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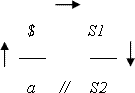
事实上,拉康的四类话语并无固定的先后,但四种角色之间各自相对的次序是固定的,因此可以通过逆时针的运转呈现出以上的四种模式。齐泽克认为,四类话语理论的“整体构建基于符号复制,将一个实体复制到它自身和它在结构中占据的位置。因此,主人话语必定是出发点,因为其中实体与位置是重合的”(主人作为动因即是话语模式的原初结构)。
在拉康的理论中,前两种话语模式,也就是主人话语和学院话语,代表了宰制形态的话语。在两种总体化话语中,主人话语无疑是更为强势的,因为它是以绝对武断的主人能指为动因的;而学院话语中的动因是知识,他仍然需要主人能指的支持。齐泽克则认为学院话语的两种基本形式是资本主义与官僚极权主义(包括斯大林主义)。从这个意义上说,似乎只有中国的威权主义可以被视为主人话语的典型体现:意识形态威权主义不同于官僚极权主义,在于这种主人话语的形式,即使在某种极度规训化的状态下,也主要不是通过警察制度的手段来达成操控的,而是通过领袖的魅力,通过主人能指本身的绝对价值和可认同性来构成的。因此它的形态可以由这样的图式来标示:
政治集权/威权(S1)
→
教育、理论(S2)
—————— ——————
激情/禁欲主体($)
意识形态(a)
在主人能指之下,必然存在着某种被激情与禁欲所分裂的主体,这种主体是对主人能指的隐秘支持。比如说,以电影《霸王别姬》、《活着》和《阳光灿烂的日子》为例,我们便可以从对文革的截然不同甚至相反的影像或叙事表达中找到这种分裂主体。《阳光灿烂的日子》中的马小军就在这种政治激情(在撬门锁、爬烟囱、跃下跳水台等段落中对英雄主义的象征性追求与失败)和社会禁欲(对女性的追求和遭弃)的双重煎熬下成为主人能指的坚强后盾。如果说《阳光灿烂的日子》表达了这种主体的阳光形象,那么那些具有悲剧意味的同样凝聚了这种分裂的主体性:在《霸王别姬》中,这样的主体性不是由段小楼和程蝶衣承担的(他们丧失历史主体性的专政对象),也不是由《活着》里的福贵和家珍承担的(他们是被历史拖曳着前进的,缺乏主体性的躯体);而是由以《霸王别姬》中的小四及其伙伴和《活着》里的万二喜及其同事所拥有的——他们被禁的隐秘欲望只有在批斗大会(升华了的暴力)或画领袖像(替代了两性间性爱的升华了的爱)的狂喜中才能抒发。这样,作为主人话语效应的意识形态(那个齐泽克称为崇高客体的),恰好与左侧的分裂主体呼应,而形成拉康的幻想公式:$<>a,标示了主体在面临作为小他物的意识形态时的(不可能的)欲望,也可以说,意识形态以魅惑的样式反过来成为主体的幻想,因而主体则只能处于分裂的状态。
在中国的历史文化语境下,如果说主人话语是毛时代的基本话语模式的话,那么在后毛时代,可以说,学院话语占据了社会文化场域的主导地位。齐泽克把学院话语称作是“现代性的霸权话语”。在这里,学院指的是一种包括了知识体制、科学体制在内的社会体制,因此拉康曾经将前苏联政权界定为严格意义上的学院话语统治。不过,在当代中国,在动因位置上的是S2不是官僚机构或警察制度,而是资本和商业体系,它在极大程度上支配了当今社会话语的整体运作。这个学院话语的图式可如下标示:
资本/商业体系(S2)
→
商品(a)
——————
——————
历史终极(S1)
犬儒主体($)
我以为,在拉康的学院话语图式中,有意思的是S2仍然是由S1所暗中支持的,这同当今中国社会主流话语模式的基本面貌完全吻合。也可以说,中国的资本和商业运作体系比起其他地域的市场制度来,更加不具备内在合理的、纯粹的自身逻辑性。这个体系的可建构性和可操作性从根本上说来自于它赖以依托的“看得见的手”——而我指的并不是具体的政治体制,而是政治文化的话语元素,也就是关于历史终极的宏大规划。这个规划的具体蓝图可以由不同的“主义”来命名,而商业主义恰好是当今全球文明似乎最为有效能够完成这个蓝图的可能的秩序。资本/商业体系所创造的着名“小他物”当然是那个叫做商品的东西。齐泽克曾经以资本主义成功的商品范例可口可乐来说明小他物的特征:“你喝得越多,你就越渴”,或者“你越是拥有它,缺乏得就越多”——这显然也是商品的一般和根本特性。资本/商业体系还通过商品反讽式地抵达了学院话语的最终产物:主体,但不是被规训的主体,而是商品原则之下暗藏的犬儒主体,它意味着作为质的主体的异化。由于商品以等价原则和量化标准取消了价值判断,犬儒主体也同样泯灭了一切包括正误、善恶、优劣在内的差异。当代中国的犬儒主义社会思潮典型地代表了历史终极的主人能指经由资本和商品体制的话语体系的作用,如何以一种被戏仿的样态呈现出来。
在主人话语与学院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的社会话语结构下,另外两类话语形态——分析师话语和癔症话语——具有某种构成某种对应或歧异的力量的可能;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来探讨,中国当代的文化诗学作为一种公共领域中的特殊话语,如何可能被拖曳或参与到文化政治的话语运作过程中。其中,“分析师话语”似乎理应是一套代表了精神分析学基本价值的话语,而拉康也的确曾将分析师话语视为具有与心理和社会压迫相对立的功能。在分析师话语中,占据动因地位的是“小他物”,也就是拉康理论中的剩余快感(plus-de-jouir),或痛快(jouissance),是基于在晚期拉康的精神分析理论中,分析师所占据的地位不再是绝对权威的“大他者”,而是激发欲望的“小他物”,他和被分析者(癔症病人/分裂主体)形成了a<>$的关系(这正是分析师话语图式的上半部分所显示的)。分析师作为分裂主体的小他物,意味着他诉诸癔症病人的是一种能够不具有压迫感和控制力的因素。在这里,作为小他物的分析师角色并不绝对意味着被符号秩序疏漏的实在界残余,而是占据了剩余快感位置的,为分裂主体而存在的欲望原因-目标。不过,a<>$的公式在拉康的理论中还有另外的含义,它同时也指示了与幻想公式相反的倒错公式;换句话说,分析师话语的结构与倒错话语的结构是一样的。那么,按照齐泽克的说法:
倒错的社会链接和精神分析的社会链接之间的区别是基于拉康的小他物概念的强烈暧昧性,这个概念同时意味着想像的、幻想的诱惑和屏幕和这种诱惑所遮蔽的,那个诱惑背后的虚空。因此,当我们从倒错过渡到分析的社会链接时,动因(分析师)将自己减为空虚,以激发主体直面他欲望的真实。
那么,在当代中国文化的话语场内,我以为分析师话语/倒错话语的动因也可以被看作是具有双重向度的。首先,分析师话语几乎可以对应于现代启蒙话语,假如精神分析师的角色与启蒙者的角色可以类比——二者都试图通过言说的途径,治疗处在某种精神困扰状态下的个人——前者的对象是精神病患,后者的对象是处在历史变迁中的迷惘主体。正如精神分析师把自己置于一个通过激发病患欲望以祛除压抑的位置,启蒙者同样是以唤起受到精神压抑的,或仍然处在蒙昧状态中的主体。在拉康早期的理论中,精神分析师所占据的是“大他者”的地位,精神分析的移情等同于符号化的同一;而晚期拉康则将精神分析师看作是“小他物”,他不再以父法的形象显现,而是本身就蕴涵了空缺、错位、破碎,并以此催生填补的欲望。在当代中国的文化和文学场域,启蒙者的形象,乃至启蒙话语本身,也经历了类似的变化。这种启蒙话语,可以用拉康的图式来这样表述:
(后)启蒙主义(a)
→
被压抑的主体($)
——————
——————
人文科学(S2)
乌托邦(S1)
这个图式的原初表达可以是启蒙现代性作为动因的积极构成。不过,当代文学中对于启蒙主义的表达跳脱了二十世纪文学主流的模式——比如《家》、《青春之歌》以至于《艳阳天》——从而通过呈现出符号界的缺漏与创伤的幽灵,以否定的方式来言说未完成的现代性的话语,因为这种未完成不是目的论的前奏,而恰恰就是现代性本身的必要形态。比如在王安忆的《叔叔的故事》中,不但叔叔作为启蒙者的形象无法与自己的角色同一,小说叙事作为启蒙主义的必要手段也呈现出截然不同的面貌。在小说的一开始,叙事者便声称:“这是一个拼凑的故事,有许多空白的地方需要想象和推理,否则就难以通顺。我所掌握的材料不多且还真伪难辨。”但空白和碎片化,却反而具有对受到符号化阉割的主体的解放功能。王安忆的《启蒙时代》在标题上就涉及了启蒙的主题,用作者自己的话来说,它“是一个写思想的故事。”不过吊诡的是,王安忆又同时认为,小说所书写的是文革时代,而她“个人不以为这场文化大革命有多少思想含量,……它并没有留给我们什么思想果实”。换句话说,她通过展示“没有思想”来“写思想”。这也是为什么有论者认为这部小说“气韵衰微”。但也许不妨说,这种“气韵衰微”就是叙事风格上的低调,摒除了经典启蒙叙事激情的是另一种激情,一种作为匮乏、厌倦和丧失的激情。同样,对于韩少功来说,《马桥词典》的启蒙性不在于教化。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马桥词典》对现代中国文学的启蒙母题创作的发展,反而在于启蒙话语的自我错位,在于“将祛魅与含魅这两种逆反的叙事意向结合在一起”。正是这种后启蒙主义具有自身沟壑的矛盾形态,而不是作为符号秩序的启蒙法则,才成为压抑主体的欲望原因-目标。也就是说,未完成的现代性只有从否定的意义上才能够迫近启蒙话语的终极效应——乌托邦。
不过,如果我们把拉康对于倒错话语的论述纳入考量,与分析师话语相同的话语图式则展示出了潜在的危机——所谓“想像的、幻想的诱惑和屏幕”——齐泽克认为这是拉康对于分析师话语的一种“激烈的自我批判”。在倒错话语的中,作为动因的小他物占据了倒错者的角色,是“痛快意愿”的执行者。倒错者从定义上便是将大他者的痛快当作自身的痛快来追逐的,或者说,他明知是大他者的痛快,但仍然为了满足大他者的期望而努力执行那个意愿,从而成为“大他者痛快的工具”。如果说大众娱乐是这个时代无法阻挡的话语主潮,在当代中国,这个倒错话语的图式至少可以下列形态展示:
娱乐(a)
→
异化主体($)
——————
——————
文化工业(S2)
乌托邦(S1)
从这个图式里,我们可以看到,必有体制性的存在作为娱乐的根本基础与支点,也就是说,娱乐的快感无非是为了文化工业体系的快感目的服务的。当今的娱乐话语典型地体现了齐泽克一再强调的拉康理论中的超我指令:“享乐!”按齐泽克的说法:“‘小他物’究竟在什么时候作用为享乐的超我指令?当它占据了主人能指位置的时候”。正是娱乐文化的话语性,成为对异化主体的构建。比如,超女观众所认同的并不是超女们,而是超女的评委,甚至娱乐体制本身;他们的享乐是对娱乐符号的隐秘基础的虚幻认同而获得了被阉割的、分裂的主体性。而作为娱乐符号的超女形象由于其(非专业的)缺憾的特性成为唤起欲望的幽灵:它替代主人能指,占据了话语动因的位置,迫使观众进入娱乐的话语场域,从而成为无法与自身概念相符的异化主体。因此,娱乐话语所制造的是一种虚幻的乌托邦:它是娱乐工业所允诺的大同、自由或幸福幻景。
直接呈现出分裂主体的,便是拉康称之为癔症话语的话语形态。在当代中国,没有什么比先锋文学和前卫艺术更能体现出癔症话语的基本面貌了:先锋话语就是一种支离破碎,语无伦次,甚至不知所云的言说方式。如果说启蒙话语能够以否定的方式展示出现代性的危机的话,先锋话语则直接诉诸了后现代诗学,比如残雪的胡言乱语,莫言的狂言呓语,等等。如下列图式所示:
先锋文学/前卫艺术($)
→
文化范式/文学经典(S1)
————————
——————
创伤记忆(a)
解构的认识论(S2)
在这里,先锋话语的言说对象是作为主人能指的文化范式/文学经典,它剧烈地撼动了经典的原有构成,同时也创造出新的文学范式。正如齐泽克所言:
在主人话语中,主体的身份是由S1,即主人能指(他的符号性头衔-委任权)来担保的,它是界定主体伦理尊严的忠诚。对主人能指的认同导致了存在的悲剧状态:主体尽力将对主人能指的忠诚——比如,忠诚于赋予他生命意义和整一性的使命——保持到最后,但他的努力由于抵制主人能指的残余而最终失败。相反,有一种滑动游移的主体,它缺乏主人能指中的稳定支持,它的整一性是由同纯粹的残余/垃圾/盈余之间的关系,同‘不体面’的、内在喜剧性的、实在界的星星点点之间的关系而维持的;这样一种对残渣的认同当然就引入了存在的模拟喜剧状态,一种戏仿过程,不断地颠覆所有坚实的符号认同。
在这里所说的维持动因的那种关系中,“纯粹的残余/垃圾/盈余”或“‘不体面’的、内在喜剧性的、实在界的星星点点”无疑就是作为小他物的创伤记忆,它是先锋话语的历史起源,注定了先锋话语的动因是遭到创伤化的癔症主体。齐泽克所强调的“戏仿”式的“颠覆”揭示了先锋话语激进的社会意义,表明了“滑动游移的主体”绝不是一种纯粹的游戏主体,对符号秩序的重组恰恰体现了一种强烈的现实感——只要我们承认当代中国的“现实”是在相当程度依附在符号秩序上的。那么,所谓的“模拟喜剧”就不是传统文化政治中的“颂歌派”或“谴责派”,也不是保守派或激进派——也就是说,现实既不可能加以维护,也不可能遭到铲除,而是一种征引与瓦解同时作用的对象。换句话说,符号界是无法逃脱或弃绝的,当然也更难以认同;先锋主体的分裂性在于它处于被这两者撕扯的中间,只能置身其中,揭示符号与其意指或内涵的错乱,并把这种错乱承担为自身的错乱。莫言的血腥,残雪的荒诞,阎连科的诡谲,无不体现了这种置身于错乱的癔症主体性。可以看出,这样的癔症话语形态并非是纯粹消极的,它最终给予了我们一种新的知识,一种建立在解构原则基础上的认识论。
应该说,分析师话语(文学中的后启蒙话语)与癔症话语(文学中的先锋话语)都能够看作是对主人话语与学院话语的回应,也就是对中国现代性的反思,在当代公共文化领域发出独特的声音。在这里,一种激进的文化政治不再是直接的政治理念或政治意念的具体表达,而是在话语元素的种种关联与呈现中体现出较为复杂的政治意味与政治向度。文学中的文化政治的参与是建立在如何加入到话语体系的动态网络中这样一个问题(而往往不是一个确定无疑的结论)的基础上的,而不是自以为能够置身其外,以为能够建立一套元话语来替代传统的或现实的话语体系。元话语只是主人话语的另一个代名词。那么,只有返回自身话语性的,揭示了其非同一性与解构性的批判话语,才是文学政治向度的积极体现,标志着文学内在的社会功能,而不是传递着外在的政治信息。
《自由写作》首发
回到开端
|